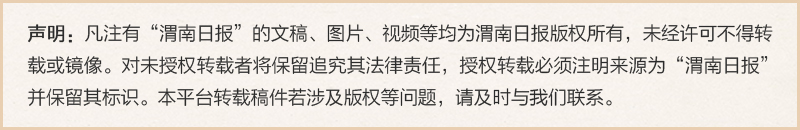渭南日报 记者 吕洁 实习记者 王安瑶\文 记者 党骁\图
黄河之水自黄土高原的沟壑间奔涌而出,在韩城市西庄镇的塬岭褶皱里,滋养出一方承载千年文明的土地。登上柳枝村望春楼凭栏远眺,但见黄河如鎏金缎带环绕着起伏的塬峁,那些凝固的黄土浪涛,静静地托举着脚下这片古老村落。
这座始建于南宋的村庄,形似展翅欲飞的凤凰栖息于高原之上。村东三眼洞为凤首,村西望春楼作凤尾,南翼舒展至戴月桥,北翼延伸至牛王庙,先民以建筑为墨,在广袤大地上绘就凤凰涅槃的磅礴图景。
斑驳的青砖沉淀着岁月沧桑,古朴的石刻诉说着文明传承。时代更迭中,柳枝村如同一位睿智的老者,既守护着祖辈留下的文化瑰宝,又接纳着现代文明的滋养,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独特的光彩。

望春楼
千年古建里的凤凰印记
村里自古相传,在明朝成化年间,村北竹林寺的一株枯柳奇迹般复活,向南生长的枝条尤为茂盛,直指村落。村民视此为祥瑞,遂更名“柳枝村”,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从此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。
行至村中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历经沧桑的木牌坊。这座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市级文保单位,是韩城乡村仅存的木牌坊珍品。牌坊采用单檐悬山顶设计,两柱间“经天纬地”“浩气凌云”的匾额笔力雄浑,柱础石雕上狮下鼓的造型栩栩如生。每当夕阳西下,余晖为精美的斗拱花卉镀上金边,仿佛在诉说往昔的荣光。

关帝庙献殿
牌坊南侧的孙公祠堪称明代祠堂建筑的典范。门额“孙公祠”三个大字遒劲有力,内设列祖列宗神龛,香火绵延不息。四壁彩绘与天花板绘画仍色泽明丽,这座在时光长河中屹立不倒的建筑瑰宝,静静诉说着明代匠心的永恒魅力。
村中关帝庙建筑群尤为壮观,由献殿、正殿及华佗庙、娘娘庙等组成。庙内“庙套庙”的结构堪称一绝,四根方木柱撑起内殿,外殿环抱,形成独特的“回”字形空间。正殿东西墙上的“千里走单骑”和“单刀会鲁肃”壁画,历经数百年仍色彩鲜艳,人物神态栩栩如生。
村西的望春楼则充满传奇色彩。这座五层高的砖木建筑,既有“闺阁望春”的浪漫传说,也承载着“御匪护家”的实用功能。登楼远眺,可见黄河如带,村落似凤,将防御功能与景观价值完美融合。其结构设计精妙,虽历经沧桑,至今依然巍然屹立,是先人智慧与匠心的见证。

孙公祠正殿屏风木门
如今,虽然村中三眼洞、饮马池等古迹已消失在时光里,但现存的木牌坊、关帝庙、望春楼与四合院,仍如凤凰的翎羽,闪烁着古人与自然对话、与命运抗争的智慧光芒,成为中华传统建筑艺术的标本。
一位守护者的传承丹心
在柳枝村,有一位特殊的“导游”。58岁的孙继宁既是村医,又是义务文保员。
“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村里的文保员,他用了一辈子光阴守护这些老建筑,如今成了我接续传承的责任。”8月6日,他正跟记者细数孙家大院砖雕门楣的家族故事,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谈话。
“喂,小田啊……广州来的游客?知道义务讲解员?”他眼角漾起笑意,“好,我这就过去。”挂掉电话,他略带歉意地看向我:“记者同志,村口来了几位广州游客,说是看小红书找来的,托小卖部老板打了电话,要不咱们一起去?”
柳枝村的午后,蝉鸣裹着热浪在巷子里翻滚。我们沿村道往村口走,远远见一家三口站在小卖部门前张望,女士举着手机正拍摄村口的木牌坊。
“你们好!我是孙大夫。”孙继宁快步上前,热情伸出手。易女士惊喜迎上来:“孙老师您好!我们在小红书上刷到您义务讲古村故事,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传统村落的魅力。”
就这样,采访变成了一场特别的导览。孙大夫带着易女士一家,从凤头“三眼洞”遗址讲起,循着凤凰展翅的村落轮廓,探访一座座承载记忆的建筑。走到关帝庙前,他指着屋檐下的自动消防设备说:“这套系统花了上百万元,但我们觉得值。老祖宗留下的东西,得用最好的方式护着。”

琉璃脊饰
“您又当医生又做讲解员,太不容易了。”易女士感慨道。“这有啥?”孙大夫摆摆手,“我父亲那会儿条件更艰苦,不也守了一辈子?”
这场偶然的相遇,让我们看见柳枝村文物保护最鲜活的模样——不是冰冷的规章制度,而是像孙大夫这样普通村民的热忱与坚守。他用医者仁心呵护村民健康,更以文化守护者的担当延续着村落文脉。当游客循着社交媒体而来,当年轻一代对古老建筑生出好奇,这份坚守,便有了最珍贵的回响。
两本村史中的故土深情
阳光穿过雕花窗棂,在泛黄的书页上洒下细碎的光斑。80岁的孙智省坐在屋里的藤椅上,小心翼翼地翻开那本《古柳逢春》,指尖轻轻摩挲着书页,仿佛在触摸一段鲜活的历史。

木牌坊
2014年,这位曾经的村支书萌生了一个念头,要为柳枝村留下一部村史。“村子八百多年的历史,不能就这样随风飘散。”老人回忆道。
他很快召集了几位村中长者,成立了编写小组。起初,会议室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,老人争相讲述记忆中的往事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繁重的工作让许多人打了退堂鼓。
“他们都走了,可这事不能停啊。”孙智省独自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三年来,他风雨无阻地走访村中老人,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故事。有时为了核实一个年份,他要往返好几户人家;有时采访到一半,老人就疲惫地睡着了。最让他痛心的是,有几次如约前往,却得知老人已溘然长逝,那些尚未来得及记录的故事,永远成了遗憾。

古巷
2017年,《古柳逢春》终于搁笔。这本221页的村史,字里行间尽是老人对故土的绵长情意。尤为动人的是,书中收录了不少游子的家书——远在新疆的孙汉章写道:“六十年大漠风沙,吹白了双鬓,却吹不散心头的乡愁。”在西安定居的孙民权,字里行间满是游子的哽咽:“家乡日新月异,唯那份文化元气从未改变,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,是漂泊再远也能找到归途的根。”
这些穿越千山万水的文字,像一根根看不见的丝线,将天涯游子的心,永远系在故乡的柳梢头。也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乡愁,化作老人笔尖不竭的源泉,2019年,他又完成了更翔实的《柳枝古今人和事》。
“这两本书从不售卖,只赠予有缘人。”柳枝村党支部书记高民仙说,“每逢有研学的师生踏访,或是远方客人寻来,我们总会送上一本,希望让字里的乡愁随书页流转,把故乡的根种进更多人心里。”

柳枝村航拍图
古村寻根,寻的不仅是建筑之根、历史之根,更是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之根。在这里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座保存完好的古建筑,更是一代代柳枝村人对文化传承的坚守。
离村时回望,夕阳为古村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。望春楼上的风铃依旧叮咚作响,仿佛在吟唱:柳枝已逢春,文脉永流传。在这片凤凰形状的土地上,古老的文化正焕发出新的生机,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绽放。
编辑:马睿妮
初审:雷沛
终审:杨宇龙

 渭南发布
渭南发布

 数字报
数字报

 官方微博
官方微博

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