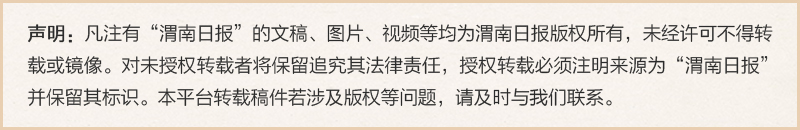师铤
中国古代史上,少小出名的文人很多。但是,儿时轶事流传近千年,妇孺皆知的人不多,司马光就是其一。
从他去世后到现在,幼童知道他,因为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人尽皆知;少年知道他,因为和他息息相关的北宋新旧法之争,是历史课重要的考点;研究古代文化的文人墨客知道他,因为他主编的《资治通鉴》,是绕不过去的经典。
司马光祖上是河内人。注意,这个河内可不是现在越南河内那个河内,这个河内指的是始置于楚汉之际河内郡,治所在怀县(今河南武陟),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。
因为司马孚的后人征东大将军司马阳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(今山西夏县),子孙便以此为家。所以,司马光的所有“官方简历”中,写得都是“陕州夏县人也”。
有意思的是,司马家这个“名人之后”的履历,颇有些“依附”之嫌。司马池,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,在《宋史》有传,开头第一句就是“自言晋安平献王孚后”,注意这个“自言”,也就是“自称是”,没凭没据的……
司马光的高祖、曾祖因战乱不仕,到了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才开始科举入仕。司马炫“试秘书省校书郎,知耀州富平县事”;后来,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“知耀州”(现在的富平县当时属于耀州)、“知同州”;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,当过郑县(当时属华州)主簿。
所以算起来,司马光一家三代都在渭南当过官。
在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刻本的《富平县志》中,说“司马炫,夏县人,温公(司马光)曾祖(此处有误,据苏轼《司马温公行状》,司马光的曾祖叫司马政,祖父叫司马炫。苏轼和司马光相识二十余年,在行状这么重要的文章,关于司马家族谱的记载,应该是权威的),举进士,以气节著,为富平令,在官未几境内大治。”就是说司马炫进士出身,以气节闻名,在富平当县令没多久,境内就非常安定了。
可惜,司马炫早逝,儿子司马池少小丧父,却年少有为,他把父亲留下的遗产全部辞让给父亲的兄弟,自己安心读书。第一次考进士时,母亲病逝。家书传来,友人害怕影响他的状态,藏匿家书隐瞒消息。许是母子连心,司马池夜不能寐,给友人说:“我母亲一向身体不好,家里咋可能没事呢?”第二天走到宫城门口,司马池徘徊不入,友人实在不忍心,告诉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。司马池便放弃科举,大哭着赶回家料理母亲后事。第二年,司马池再次应试,一举考中进士。司马池是个好官,廉洁、努力,但是他的官场生涯不算顺遂。起起伏伏中,便在渭南大地留下了他的脚步——据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《耀州志》记载:司马池,夏县人,光之父。初授永宁主簿,迁司录,以不附皇甫继明,除开封推官,敕至阁门,为继明党所沮,罢知耀州。据乾隆六年(1741年)《同州府志》记载:司马池……有文行。仁宗时知同州。性质易,不饰厨传,以清勤仁厚闻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司马池曾经担任过光山县(今河南光山)知县(司马光就出生在这个时候,他名字里的“光”就是取自“光山”)。这时候,皇宫大兴土木,诏令光州所属各县三天内完成上缴毛竹任务。当时各县均不产毛竹,三天内是完不成任务的。司马池知道就近只有黄州(今湖北黄冈)产毛竹。他请求上级放宽日限,并命下属连夜赴黄州购买毛竹,雇当地车辆送往京城开封。结果光州各县只有光山最先完成任务。因为这件事,宋仁宗记住了他。后来司马池升任凤翔知府,宋仁宗想提拔他任知谏院。司马池多次上书恳辞。仁宗不解地对宰相说:“别人都喜欢升官,只有司马池谦让,真是难能可贵。”于是硬给司马池加上直史馆长官头衔兼凤翔知府——这种“皇上要给我升职我就是不愿意”的作风,也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司马光。我们稍后就会展开。
司马池有两个儿子,一个叫司马旦,一个叫司马光。
司马光有三个儿子,可惜两个早亡,只留下了一个陪他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康。有一种说法认为,司马康其实是司马旦的亲生儿子,后来过继给了司马光,这种说法的依据是苏轼《西楼帖·与堂兄三首》中一句“司马康是君实(司马光字君实)之亲兄子,君实未有子,养为嗣也。”说起来,司马康也差点来渭南当官——“举明经中第,授耀州富平主簿,文正公(司马光谥号‘文正’)奏留国子监听读。”——编纂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项庞大的集体工程,身边留一个科举出身的儿子当校对,于公于私,都说得过去。不过要不是因为这个,司马家族就有四代人都曾经在渭南当官啦!
话说,司马旦在郑县任职时,听说当地有个有钱的妇人和人争地,被告上衙门,她买通官吏,一场官司压了十年没判。司马旦拿出卷宗一看,情伪立见,当即罢免了十几个官吏。当地有恶霸,豪欺乡里,没人敢惹,司马旦将他擒拿归案。
司马旦和司马光两兄弟一直相亲相爱。大哥老了以后,小弟“奉之如严父,保之如婴儿。每食少顷,则问曰:‘得无饥乎?’天少冷,则拊其背曰:‘衣得无薄乎?’”。
司马旦退休后住在老家夏县,当时司马光闲居洛阳,两地离得不远,两兄弟常常往来,一起探讨国事家事天下事。后来,王安石变法失败,朝廷希望老臣司马光出山收拾残局。因为变法之争对官场心灰意冷的司马光不想去,司马旦作为长兄,对他说:“生平诵尧舜之道,思致其君。今时可而违,非进退之正也。”——平时光读圣贤书说漂亮好,真到了报效朝廷的时候,推三阻四个啥!
司马光幡然醒悟。
当时,大家都盼着司马光出山,一听这事,对司马旦交口称赞:“长者之言也。”
前文说,司马家有官不当是遗传,是早在神宗刚即位,就要破格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,他力辞不从,但神宗就是不批准,还当面问司马光:“古之君子,或学而不文,或文而不学,惟董仲舒、杨雄兼之。卿有文学,何辞为?”
时年四十八岁,从二十岁中进士开始入仕的司马光,在当了二十八年官后,拒绝神宗的升职理由居然是:“臣不能为四六。”(臣不会写骈文)
神宗惜才,说:“如两汉制诏可也。”(不用搞魏晋南北朝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,像两汉时期一目了然就行。)
司马光还是不从,说:“本朝故事不可。”(咱大宋可不兴这样。)
神宗一想,不对啊,忍不住问:“卿能进士取高第,而云不能四六,何也?”(你都考上进士了,咋还说自己不会写骈文?)
司马光一听,说不过皇上,赶紧告退。
神宗不放弃,派了太监拿着升职公告一直追上去。
但是,司马光跪着,就是不接。太监急了,说:“大人啊!赶紧回去谢主隆恩吧,皇上在里边等着你呢!你不接受,咱都下不了班啊!”说完,他一把把公告塞到司马光怀里,硬推进去谢主隆恩。就这样,司马光“不情不愿”的升了职。再往后,就官至宰相了。
因为变法之争,司马光一度赋闲洛阳,那时候,他给自己盖了一所园子,取名“独乐园”。苏轼听说后,立马写了一首诗过来,诗曰:“先生独何事,四海望陶冶。儿童诵君实,走卒知司马。”这所园子这首诗,又引发了很多故事和风波,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但仅就这首诗来看,司马光为人为官,在百姓心中的威望,可见一斑。
司马光曾经对人说:“吾无过人者,但平生所为,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。”他去世后,京城开封的商人生意不做了也要去吊唁,穷人卖衣服换奠仪,灵车路过,整个巷子都是哭声。到了葬礼那天,来祭拜的百姓,哭得像自己亲人去世。不仅在京城,即使远在岭南,老百姓也相约祭拜,全国百姓都在家中挂上他的画像,吃饭前必在像前祭拜。京城很多画师就靠着卖司马光画像大赚一笔。
“孝友忠信,恭俭正直,居处有法,动作有礼”,这是《宋史》对他的高度评价,也是官方的盖棺定论。
他当得起如此评价。
后记:
写稿过程中,发现有一些出处不详的资料显示司马光曾经在华州任职。但是遍查各种年谱和官方传记,都不曾看见相关记录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熙宁年间,他曾以端明殿学士任永兴军安抚使。宋初尚未有“陕西省”这个行政划分,当时叫“陕西路”,辖区“东尽殽函,西包汧陇,南连商洛,北控萧关”,幅员极广。到王安石变法时,把陕西路一分为二,东为永兴军路,西为秦凤路,各以京兆(今西安)、秦州(今甘肃天水)为治。所以说,司马光是肯定在陕西准确说在西安当过官。另,在《司马温公文集》里有一首《石昌言学士宰中牟日为诗见寄久未之》,诗本身没什么,但是注释有一句“光华州判官”。加上文集中另有一首《华州祗役往冯翊留别楚正叔》的小诗(祗役特指官员奉命任职),两首诗结合来看,好像司马光真的在华州当过官。但是查阅多个版本《陕西通志》《华州志》,都未有相关记录佐证。希望能有专业人士答疑解惑。
编辑:马杭娟
初审:雷沛
终审:宋振峰

 渭南发布
渭南发布

 数字报
数字报

 官方微博
官方微博

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